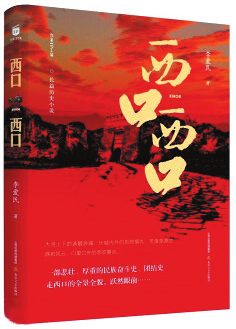
初識李愛民先生是在今年山西省作協(xié)組織的“作家回家��,集結(jié)再出發(fā)”活動中,得知他創(chuàng)作的長篇小說《西口�,西口》被列入第十一屆茅盾文學(xué)獎參評目錄����,心中暗生敬意�����。李愛民是忻州保德人��,為家鄉(xiāng)著書立傳是順理成章之事����。在這部長達(dá)三十五萬余字的作品里,作者滿懷對家鄉(xiāng)的深情��,以“河��、保����、偏三小龍”——李小朵、陳嘉豐��、郭望蘇走西口的故事為主線��,描繪了一幅波瀾壯闊的走西口歷史畫卷。
“河曲保德州�����,十年九不收��;男人走口外����,女人挖苦菜��?�!弊呶骺?����,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人口遷徙事件之一��,從明朝中期至民國初年四百余年的歷史長河中��,無數(shù)來自山西����、陜西、河北等地的人背井離鄉(xiāng)��,遠(yuǎn)赴內(nèi)蒙古����,或攬工受苦�����,或逃荒避難�,有人春去秋回,有人扎根落戶����。走西口改變了內(nèi)蒙古地區(qū)單一的經(jīng)濟(jì)社會結(jié)構(gòu),打通了中原腹地與蒙古草原的經(jīng)濟(jì)和文化通道��,融合了漢族與蒙古族的民族文化���,帶動了北部地區(qū)的繁榮和發(fā)展的同時�,也改變了無數(shù)人的命運����。
作者筆下人物形象鮮明����,個性獨特——李小朵俊美柔弱�����、重情重義����;陳嘉豐大仁大義����、心系鄉(xiāng)親;郭望蘇敦厚老實����、古道熱腸。他們身上的血性���、骨氣和道義�����,正是作者自始至終頌揚的人文精神的折射���。小說以三位主人公在黃河激流里合伙救下白進(jìn)的女兒霓歌為發(fā)端�,并以一代儒商喬致庸贈送他們的信物——玲瓏算盤和牛耳尖刀為伏線�,暗示了三人曲折離奇的命運和跌宕起伏的人生際遇,可謂“草蛇灰線����,伏脈千里”。枚是笛子的一種�����,暗示李小朵以表演二人臺小戲為生����,命運顛沛流離;玲瓏算盤寓指陳嘉豐以經(jīng)商為業(yè)�,幾經(jīng)起落,可是始終守得一顆玲瓏心���,即便富貴仍不忘扶貧濟(jì)困�、賑濟(jì)災(zāi)民���;手執(zhí)牛耳尖刀的郭望蘇一直過著刀尖舔血的生活�,先加入太平天國,后又參加義軍����,最終與女俠青婧結(jié)伴行走于大漠草原,除暴安良�����,快意恩仇����。
文中處處伏筆疊加��,線索錯綜復(fù)雜��,展現(xiàn)了內(nèi)地漢民在口外謀求生存的艱辛困苦��,以及勇于向命運抗?fàn)幍牟磺?���。書中除了引人入勝的場面描寫外�����,還始終充盈著一股浩然正氣����,這種正氣源自老百姓內(nèi)心的道德感�����。作者用詼諧文筆表達(dá)對反面人物態(tài)度的同時����,將青年男女的相愛寫得也是曲折婉轉(zhuǎn)�,唯美含蓄。出于命運安排����,三位主人公和最初的心上人都未能終成眷屬����,令人不免感傷��,好在最后都找到了自己的感情歸宿�����,給讀者略施安慰���。文中的其他人物,如蘭心蕙質(zhì)的霓歌�、率真活潑的薩日娜、敢愛敢恨的“二老財”���、隨波逐流的“四奶奶”���,也都在情感世界里嘗盡了人生的酸甜苦辣���。
書中隨處可見作者對故土的深厚感情,酸撈飯和苦菜是家鄉(xiāng)人最常吃的食物�����,土窯洞則是他們大多數(shù)人一輩子的棲息地���。老百姓在黃土地里艱難生活����,不是萬不得已也不會背井離鄉(xiāng)走西口��。小說開篇以河曲縣壯觀的河燈會場景為切入點��,結(jié)尾則重現(xiàn)包頭黃河渡口放河燈的場面�����,首尾呼應(yīng)����,仿佛一氣呵成�����。然而�,時光流逝����,世事更迭,一切早已不是最初的模樣����,令人不禁感嘆天道無常,不變的是道義人心����。
故事的結(jié)尾處,作者通過幾句讖語暗示了風(fēng)雨飄搖的清廷終將被卷入滾滾的歷史洪流中����,而這首慷慨激昂的西口長歌也終將成為過去���,只剩些許音符在歷史的長河中抑揚頓挫��,如訴如泣���?���!盀槭裁次业难劾锍:瑴I水���?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�����?����!庇冒嘞壬倪@句話來描述李愛民創(chuàng)作這部作品時的心情��,委實恰到好處�。(張彥婷)
(責(zé)任編輯:盧相?。?/span>